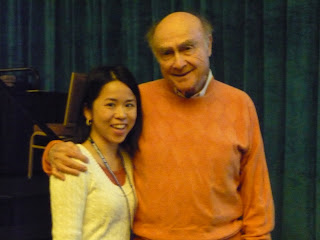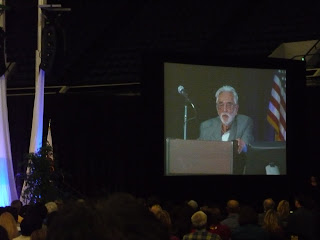跑台灣一躺,想不到變成一個非常具啟發性的小形亞洲戲劇治療師聚會。
來自日本的佐知子,是我讀戲劇治療時的同學。
雅卉還在CIIS唸戲劇治療。
然後是台灣最活躍的戲劇治療師張志豪。
在台灣,好像比較容易碰到具質素的治療師。
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,是他們比較會看到要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想法,而不是把西方老師的東西照本宣科。
在香港,比較會見到很努力上工作坊、然後把bio愈寫愈看似厲害的治療師。嘴巴就是上過誰誰誰的課,與自己拿了什麼什麼資格。誰誰誰說了什麼,然後就應該要像跟聖旨般照著辦等等等等。
但我跟在台灣的治療師聊時,好像比較容易碰見踏實地研究的人。
像我跟志豪聊了一個晚上,我興奮得整晚都睡不著。
有些東西是我一直有這個想法,但是在香港找不到人可以聊的;
有些東西真是大開眼界,是我第一次聽到,但是覺得非常有道理。
他幫我搞懂了一些事情;他令我想通了一些事情;他使我思考一些事情。
人家明明都很累了,我還是抓著人家不放。真是失禮。
但我第一次可以用華語聊戲劇治療聊得那麼起勁,都幾乎忘我了!
他的基礎厚、角度寬,而且有自己的想法。人很好、還很謙卑。用心學,但更用心玩。最重要是不會太聽話。
(我最怕跟乖乖聽話的治療師聊。治療師,尤其戲劇治療師本來就應該帶點反叛才對味。)
我跟佐知子都覺得,戲劇治療師就應該長他這個模樣。
跟佐知子聊,又有另一番發現。下一篇再來寫好了。
2009年12月19日
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 conference
第二次去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 conference。
幾千人聚在一起,吸收美國頂尖兒心理治療師們的分享。
那些,可全都是自成一體的大師。
大部份都是八十多歲的老頭兒。每句話都是智慧。擲地有聲。
大家都像追明星般去朝拜。
第一次去的時候,治療的事業才剛開始。
看到的精彩都只是字裡行間的。一句話被如此接下來,內心便己驚嘆不已。
事隔四年,累積了一些經驗和一些挫敗,重新觀看大師級的演繹,比較能看到脈絡。現在比較能像看故事般,看到治療師如何撒網,等魚上釣,從容收線。
慢慢看到治療師如何鈎主題,如何玩語言、如何用身體。
說到用身體,發現今年多個工作坊、多個大師都強調身體語言之重要。
不要被語言局限成為探索空間。演員訓練與心理治療的類同被大會主席Jeffery Zeig類比放在一起。Hamlet的獨白,還幾度被搬上舞台演繹。
什麼人適合用什麼類型的治療?
你最信什麼?你最強什麼?
像我,我好像看到什麼都只看到戲劇治療。
會中總是找新偶像。
第一次去的時候愛上了完形治療師Erving Polster。
今次則被James Hillman迷倒了。
Erving Polster是個有聽障的八十八歲老頭了。
聽是聽不清楚,人卻非常精靈鬼馬。
那年看他現場示範,百發百中,欽佩不己。
今年決定都去看他好了。看他做了六個個案,就那麼一個我有保留而己,其他都美得教人咋舌。
做治療的,跟做理論的,應該真是兩伙人。
Polster在示範前說點理論,他說有三個大點。但說了兩個就老是想不起第三個,還喃喃自語:「我明明想好三個的。」
理論,是用來溝通和傳授的,而不是用來做治療的。
James Hillman是jungian Psychologist。
Jung的東西,太神了。你知道是好東西,但實在太遙不可及。我甚至懶得假裝我懂。
James Hillman有一個比較近代的演繹。一口氣買下他三本書。希望自己真能讀下來。
有一場工作坊是辯論到底心理治療是藝術還是科學。
這兩位我的偶像,當然是偏向藝術這邊。
聽了就爽。
Minuchin真是老了。四年前的跳脫一去不返。抖著手拿水樽的樣子,教人唏噓不己。
Yalom也老了。他寫書很好看,但實在不是一個演講的明星。行將就木,更感焦慮。用兩小時借我們的耳朵訴說自己的一生,怎麼看都有種死亡焦慮的味道。<凝視太陽>是不是他自我治療的一著?
Violet Oaklander也是八十多歲。超可愛。演講多年才第一次用powerpoint。她說是孫女兒幫她弄的。看她用powerpoint的樣子,興奮程度直迫她分享的兒童個案如何在她的治療中玩遊戲。
Aaron Beck,接近九十歲。人因事來不了,卻能一手一腳搞上網,現場直播跟我們對話。思路之快、說話之清晰,幾乎比她在場的女兒更甚。
如此快樂、如此豐盛、如此可愛、如此自在的一群老人。
但願到我年老時,也能如此。
2009年11月17日
什麼人不適合接受戲劇治療?
不時有人問我,什麼人不適合接受戲劇治療。
以前我老是回答其實問題並不在戲劇治療,而是在用戲劇治療的人。
可最近再省思,卻發現還真有一群不適合者:
對生活及自我都非常滿意,或無意欲探究自身的人
心理治療常說,不要去搔未癢之處。
你過得好端端,幹嘛沒事找碴呢?
誤會戲劇治療是治療演戲錯誤的人,定必失望而回(真有這些人的);
誤會戲劇治療是以授課形式耳提面命地送你心靈雞湯的人,也會過得迷惘;
誤會戲劇治療是魔術能趕走隱霾的,固然無法適應;
但最錯誤的卻是以為戲劇治療可以用來灌輸主辦者既定信念的情況--主辦者與參加者都注定要碰一鼻子灰。
有這樣的人嗎?
通常那都是因為主辦機構在找我與找參加者之間,進行了嚴重錯配。
再加上欠缺溝通的空間,又沒有彈性的處理,便會出現上述情況。
那是三失的局面。
主辦單位、參加者與我,都不愉快。
前陣子跟友人聊起最愛面對的個案族群,我想也甭想的說是癌症病患。
我當時以為原因是這個族群給我的滿足感最大。
細想,最重要的原因,原來是為癌症病患提供服務的機構,與我的治療信念最夾。在這些機構工作時,我才感到自己真正做著我心目中的戲劇治療。
在學校面對孩子時,多多少少有點教育與輔導的味道。我做了就是做了,也沒有什麼。除非他有情緒或家庭問題,我的勁兒才來。
我對帶活動、教育與輔導都沒有多大興趣。
我對心理治療最大的興頭,原來是陪伴黑暗。
而癌症病患的機構,全部都跟我抱著相同的觀念──視戲劇治療為真正的心理治療。
主辦單位的用心純粹。
對病人了解而同理。
願意對戲劇治療作出更深入的認識,有溝通有彈性。
而病患全都在水深火熱之中,意即與死亡曾經擦肩而過。
陪伴、舒緩與轉化才有意義。
我的所學所知所想所感才有用武之地。
我做得最起勁。
最沒有勁的,是半帶商業味,或拿戲劇治療的名字來招搖的機構。
一不小心接受了這些機構的邀請,全程礙手礙腳,不對勁兒。
他們要不就找來一群想學戲之人、
要不就找來一群沒事兒塞時間的人,
要不就找來一群被洗腦的人。
施的與受的同樣無奈。
我跟你玩,好像浪費你時間;
我跟你講自省,你又覺無聊。
錯也不在你,紅娘牽錯線。
每次碰釘,都像上了一堂課。
那些一開始便沒有搞清楚什麼是戲劇治療,也沒有花時間來聽我講解的工作邀請,真的不要再接了。
以前我老是回答其實問題並不在戲劇治療,而是在用戲劇治療的人。
可最近再省思,卻發現還真有一群不適合者:
對生活及自我都非常滿意,或無意欲探究自身的人
心理治療常說,不要去搔未癢之處。
你過得好端端,幹嘛沒事找碴呢?
誤會戲劇治療是治療演戲錯誤的人,定必失望而回(真有這些人的);
誤會戲劇治療是以授課形式耳提面命地送你心靈雞湯的人,也會過得迷惘;
誤會戲劇治療是魔術能趕走隱霾的,固然無法適應;
但最錯誤的卻是以為戲劇治療可以用來灌輸主辦者既定信念的情況--主辦者與參加者都注定要碰一鼻子灰。
有這樣的人嗎?
通常那都是因為主辦機構在找我與找參加者之間,進行了嚴重錯配。
再加上欠缺溝通的空間,又沒有彈性的處理,便會出現上述情況。
那是三失的局面。
主辦單位、參加者與我,都不愉快。
前陣子跟友人聊起最愛面對的個案族群,我想也甭想的說是癌症病患。
我當時以為原因是這個族群給我的滿足感最大。
細想,最重要的原因,原來是為癌症病患提供服務的機構,與我的治療信念最夾。在這些機構工作時,我才感到自己真正做著我心目中的戲劇治療。
在學校面對孩子時,多多少少有點教育與輔導的味道。我做了就是做了,也沒有什麼。除非他有情緒或家庭問題,我的勁兒才來。
我對帶活動、教育與輔導都沒有多大興趣。
我對心理治療最大的興頭,原來是陪伴黑暗。
而癌症病患的機構,全部都跟我抱著相同的觀念──視戲劇治療為真正的心理治療。
主辦單位的用心純粹。
對病人了解而同理。
願意對戲劇治療作出更深入的認識,有溝通有彈性。
而病患全都在水深火熱之中,意即與死亡曾經擦肩而過。
陪伴、舒緩與轉化才有意義。
我的所學所知所想所感才有用武之地。
我做得最起勁。
最沒有勁的,是半帶商業味,或拿戲劇治療的名字來招搖的機構。
一不小心接受了這些機構的邀請,全程礙手礙腳,不對勁兒。
他們要不就找來一群想學戲之人、
要不就找來一群沒事兒塞時間的人,
要不就找來一群被洗腦的人。
施的與受的同樣無奈。
我跟你玩,好像浪費你時間;
我跟你講自省,你又覺無聊。
錯也不在你,紅娘牽錯線。
每次碰釘,都像上了一堂課。
那些一開始便沒有搞清楚什麼是戲劇治療,也沒有花時間來聽我講解的工作邀請,真的不要再接了。
2009年11月7日
2009年10月28日
一爿小店
說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在香港發展得非常好的音樂治療師。他既有自己的治療中心,也引來很多媒體的訪問,他大概分享了不少他的成就。而我那半堂課,則比較著重跟學生們玩在一起,讓他們感受戲劇治療。
可能因為強烈的對比。下課之後,幾個很熱心的男學生圍攏過來問我:你們戲劇治療為什麼不成立協會?多點推動、多點宣傳,才廣為人知嘛!
事實上,這幾年來,每逢遇見對戲劇治療很熱心的朋友,總會如此勸導我。
我卻是每次聽到都嚇得心肝兒噗通噗通跳。好像欠做了什麼功課給人逮個正著似的。這些年來總是在半推半就、半做不做中盤迴。
真到這天,一位溫柔的女同學替我回應的話,卻全解了我心結:「她都不是這樣的人,人人性格不一樣嘛!」
就是啊!
我根本不想要做推動戲劇治療的工作。這跟我的性格大相逕庭。
有人的性格是具野心的,要開大型的百貨公司。讓人人知曉,讓盈利最大。
但我不是做大事的人,只愛開一爿小店。有熟悉的味道,相知的客人。每件貨品都有感情,每個客人都有故事。不會有很多人知道我,但知道的都是好朋友。客源不用多,夠就好。一家窩心小店較合我的脾性。
人怕出名豬怕肥。
這些年,推過幾次電視訪問。美其名是不適合拍攝(也是啦),其實卻是我真的不愛做這樣的事情。我會很緊張。
我只愛跟我的個案深入的互動。
沒有興趣和很多人作淺淺的接觸。
事實上,這是我要去當心理治療師的原因。
安靜專注地跟「人」接觸。
如果我愛作宣傳,當初留著當廣告就好。
如果我愛出風頭,當初留著當演員就好。
沒有。
我只愛在我的小店裡做小小的事情。
默默地做我真心愛做的事情,那就很好。
為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努力鑽研,那就很好。
我不享受當「祟光」的風光,卻享受做「泰八郎眼鏡」的溫情與專注。
這陣子,還有額外驚喜。幾個不同的來源告知我,我的聲譽還不錯。那就是最大的花紅了。
這也讓我加倍認清,於我,只要繼續做我應該做的事情就好。不要節外生枝。
謝謝那位女同學的看見與接納,我的心由是安定。
不是說,不用做這些事情。
但,那.大概.不是.我.的使命。
認清了,就鬆一口氣。
訂閱:
文章 (Atom)